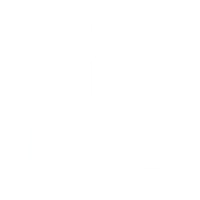1 引 言
进行情报学变革已成情报学界的共识。2017年度举行的华山情报论坛(西安)、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南京)、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北京)等情报学发展研讨会,以及情报法、《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定位南京共识》的出台,反映出此项任务的迫切性。2017年4—6月,《情报杂志》分三次以焦点话题的形式探讨了情报学学科建设问题,累计十余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国外学界对此也开展了一定探讨,其核心是“Intelligence Studies”是否已经具备发展成为“Intelligence Discipline”的资源条
件[1,2] 。情报学的发展深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每一次信息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工作的发展。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情报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深刻,这已引起情报学者的广泛探讨。如苏新
宁[3] 提出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理论要重建;曾建勋等[4] 从信息资源内容构成、信息组织方式、情报分析方法及服务功能拓展四个方面诠释了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新的核心内涵;彭知辉[5] 分析了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情报学“学科基点→学科理论基础→学科归属”的“变”与“不变”;韩毅等[6] 认为,大数据时代情报学既应坚守历史演化所积累的学科特色,也应积极响应时代挑战,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由于历史遗留、管理体制和学科资源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情报学未来的发展之路注定曲折而坎坷。本文试图延续上述研究,探讨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科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如何基于大数据思维来谋划情报学科发展,为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2 大数据给情报学学科发展带来的影响
对于情报学而言,大数据带来的影响涉及可用于情报分析的数据源的极大丰富、情报学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的变革、大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的情报学移用,以及情报学学科组织与学科应用的显著变化等。这种影响下,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2.1 大数据对情报学学科思维及研究范式的影响
1)情报学受“数据思维”的影响
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是越来越细化的学科分支和越来越专深的研究内容,情报学研究的对象逐渐走向综合、多元和细化。大数据重整体而非抽样、重效率而非精准、重相关而非因果的数据分析理念,颠覆了以往情报分析的模式,革新了它的理念,拓展了它的研究对象,毕竟,如果致力于解决航海家安全航行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和“去哪里”显然比“为什么”更重
要[7] ,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大数据的思维模式就已经作为有利的补充渗入到情报学的研究中来。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对于数据的处理既息息相关又各具特色,大数据通常处理系统中的已有数据,致力于挖掘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来发现价值,忽略个体信息的真伪;而情报分析对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应用动机更多地强调数据之间的互补与印证。大数据分析强调大而广,情报分析强调精与深[8] ;大数据处理PB级别的数据,情报分析应对海量数据;大数据分析关注相关性,情报分析重视因果性;大数据分析多源化实时的数据类型,情报分析处理样本化历时的文本文献。可见,大数据时代对于情报学的影响并不是螺旋替代的,而是交错互补的。有了这种融合与补充,情报学就可以从处理国家高精尖设备的参数数据,拓展到应对用户与销售信息的传感器数据。情报学甚少对实时性和历史性数据加以区分,它虽然也跟踪实时动态的新数据,但更多地使用对规律性总结和趋势性分析更加适用的延迟与阶段性数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情报学期刊、报告中常见“21世纪以来”、“近五年”等字眼的原因[8] 。大数据时代,预测缺失项目信息和事物发展轨迹的预见性研究,对情报学知晓结果模式下的填充式研究成为有力的拓展与补充。当情报分析面对的难以界定和精确描述的信息时,大数据思维可助其更新变量,处理“你不知道什么是你不知道的”问题,探索“未知的未知”[9] 。2)情报学受“计算思维”的影响
可见,大数据对情报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大到理论方法,小到数据本身,无孔不入并无处不在。从这个层面来看,大数据对于情报学的意义显然是从思维理念渗透到学科指导。正如李广建教授于2017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年会上所言,大数据时代将数据与信息分析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多源数据融合的思维理念,使情报研究洞察到同一事物的规律可能隐藏在不同的数据集中,不同的数据集也可以反映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对于解释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而言,无疑是全面而深刻的。大数据时代带来了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第四研究范式对社会科学同样意义深远,它推动了计算社会科学的产生,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情报学所涉及的系统开发、用户信息行为等研究皆具有较强的计算性,因此,情报学受大数据环境下“计算思维”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影响不仅涉及情报学用建模减少人工干预的研究方式,还包括情报学传承既有方法,融入计算的知识体系。它突破了人收集、处理和分析庞大信息的自然局限,以计算机、机器学习、知识理解等计算与智能分析技术为工具,用数学模型进行组织并识别情报学的计算。可见,大数据思维对于情报学的影响不是锦上添花,更趋于一种颠覆性的变革。
3)情报学受“泛大数据化”的影响
上述是情报学在大数据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但挑战同样并存:首要的问题就是理论基础的定位、技术方法的识别,这些问题如不厘清,就永远牵扯不清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的关系。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一方面要通过自适应的方法来应对外界极度不确定性的挑战,另一方面要秉持和坚守自身的特征属性。“用数据说话”并不等同于“数据即是客观事实”,大数据不是人类社会的翻版镜像,情报分析如果过分依赖于大数据提供的侧面反映,就会陷入“预测已知而忽视未知”的误区。如果说大数据只能回答“是什么”,而不能解密“为什么”的话,那么自开源情报时代以来,我们一直坚守的人工干预的原始特征就是不可或缺的。在享受大数据带来机遇的同时,情报学也要警醒自己避免“泛大数据化”研究带来的挑战,未来我们要培养的人才永远都是情报学家,而不是大数据分析师。
2.2 大数据对情报学学科组织及学科应用的影响
大数据对于情报学学科组织与学科应用带来的影响十分显著,这从大数据时代前后的情报学特征比较中可见(表1)。
表1 前大数据与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发展比较
情报学学科关键要素 前大数据时代基本特征 大数据时代基本特征 学科组织 学科应用 学科组织 学科应用 规划管理 目标定位:“文献情报学”、“信息情报学”
学科主体:高等院校
学科建设:图书情报一体化
支撑图书情报学学科发展 目标定位:“数据情报学”、“智慧情报学”、“工具性情报学”
学科主体:学界与业界协同
学科建设:与数据科学融合、与智能科学融合、与智库融合
重构情报学学科、融入大数据战略 理论体系 信息源:小样本、结构化、指定来源的文献与知识;历史信息;事实性信息
主要任务:文献与信息的检索、组织和分析;文献与信息向知识转化;提供知识服务
所涉学科领域:图书馆学与情报学
考察正式科学交流中的科学传播网络与规律;为文献与信息检索、组织和分析提供依据 信息源:多类型、分布式、大体量数据资源;实时性数据;事实+研判性数据
主要任务:数据的清洗、数据的关联分析、数据的聚合与融合;数据向情报、智慧转化;提供决策支持
所涉学科领域:跨领域
考察正式与非正式科学交流中的科学传播网络与规律;为广泛分布的数据关联性组织、多源融合与聚合提供依据 方法论 信息资源建设;为归纳性分析提供依据;为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提供支撑 情报工具开发;为预测性分析提供依据;为基于数据的情报发现提供支撑 情报流程 为固定的情报生命周期提供依据 为工程化思维应用和“假定—验证”模式的动态化情报生命周期提供依据 教育体系 培养信息组织型、知识服务型人才 培养高端情报应用型人才 1)大数据对情报学学科组织的影响
前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方法论、情报流程和教育体系,面向的是结构化文献与知识,这些大多为指定来源的小样本信息,并以历史存在的事实性信息为主要对象。其主要任务是针对文献与信息的检索、组织和分析并转化为知识来提供服务。情报学学科目标定位于“文献情报学”、“信息情报学”,高等院校是学科建设的主体,情报学发展局限于图书情报一体化。大数据时代,情报学进入跨领域(跨界、跨学科)融合发展阶段,情报学面向多类型、分布式、大体量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源存在于各种媒介的数据、文本、社会网络关系中。它们是实时动态变化的,既包括事实性数据,也包括通过语义关联、时序关联等分析挖掘而成的研判性数据。这个阶段,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多维、多结构、多来源、多类型数据的清洗、关联性分析,以及聚合与融合化组织,来实现数据向情报的转化,从而为政府、企业等提供决策支持。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目标定位于“数据情报学”(作为数据序化与转化的组织者)、“智慧情报学”(作为数据情报价值的统领者)、“工具性情报学”(作为数据分析的指引者),学界与业界(情报机构、大数据企业)协同作为学科建设的主体,并将情报学与数据科学融合(吸收数据科学理论与方法)、与智能科学融合(设计智能技术应用模式),以及与智库融合(用数据组织与分析构筑桥梁)作为学科建设的基本策略。
在情报学理论体系中,情报学的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文献增长律和文献老化
律[10] 等经验定律,离散分布原理、相关性原理、有序性原理、省力原理、小世界原理和对数透视原理[11] 等基本原理,以及与情报组织、检索、分析和技术应用等相关的理论等,均为前大数据时代提出的,多建立在具有结构化特征的小样本文献和知识基础上的应用。大数据时代,科学的交流模式和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革。非正式交流的形式日益丰富,OAJ、OA仓储、学术博客、网络社区、即时交流工具等蓬勃兴起,文献之间的引用与共享不再是科学交流的唯一方式。同时,科学研究进入数据密集型范式,原有的文献管理和知识管理进入数据管理阶段。数据组织、数据转化、数据融合成为情报产生的基础,元数据、数据获取、数据关联与聚合等技术颠覆了文献与知识的组织与转化;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方法论的决策复杂性、相关性和战略性等特征尤为显著,以计算为主的多源融合型情报、以数据为基础的工程化情报、面向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情报[12] 等成为支持决策的主要途径。(大)数据分析、文本分析、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移动媒体分析等均将成为情报支持决策的重要依据;数据聚类、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空间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可视化技术等[13] 大数据分析方法对传统的情报学方法予以补充。2)大数据对情报学学科应用的影响
前大数据时代,面向应用的情报学理论体系重点考察正式科学交流中的科学传播网络与规律,针对文献与信息的检索、组织与分析;情报学的方法论在信息资源建设中发挥作用,为基于现实问题的归纳性分析提供依据,为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提供支撑;情报流程可以概括为以情报用户为核心,以情报规划、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分析、情报应用、情报反馈等为流程的基本环
节[14] ,这些流程基于经验和历史模式,无法保证未来出现的现象会历史经验中找到答案[15] ,对预测性情报分析效用欠佳;情报学教育体系重点培养信息组织型、知识服务型人才;情报学的规划管理致力于支撑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大数据时代,面向应用的情报理论体系考察科学传播网络和规律,着眼点不仅限于正式科学交流的模式与手段还包括非正式科学交流。它针对时空维度(历史、现实、实时)及广泛分布(各种媒介、各种类型和结构)数据的关联性组织、多源化融合与聚合;情报学方法论应用于智能化情报工具的研发,为预测性情报分析提供依据,为基于数据的情报发现提供支撑;情报流程突破固有模式,工程化思维嵌入到情报流程的各个环节,“假定—验证”模式贯穿于情报流程的始终;情报学教育体系侧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使其成为数据管理者,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提出有效的决策[16] ;情报学的学科规划管理侧重于重构情报学学科、融入国家大数据战略。对于经验性规律而言,科学研究成果传播与共享的载体由文献资源拓展到网络资源,并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科学交流,小规模数据环境下测定的用于反映科学交流特征的期刊分布、作者分布和文献分布规律在大数据环境下的适用性有待于验证;在基本原理中,原有的文献序化、向知识转化以及社会网络关系的考察,将进一步拓展到更加广泛的数据组织、向情报转化,以及数据关联或非正式科学交流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揭示;在应用性理论中,情报检索与分析将突破文献的信息检索手段,向智能化、需求化检索转化。大数据时代,不仅需要对传统情报学理论体系,特别是基于DIKW链变革原有的理论体系,进行改造升级,还需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开发情报工程
学[17] 、“数据情报学”[18] 等新的理论体系,使其满足数据向情报转化的需要。3 基于大数据思维的情报学学科发展对策与建议
3.1 大数据环境下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1)学科定位:数据流中的Intelligence Studies
20世纪中期,信息爆炸催生情报
学[19] ,情报学在当时遏制和测量信息爆炸、开发信息检索系统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0] ,由此也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大数据时代,情报学的学科定位已发生变化。马费成教授在2017年“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上的报告中,将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定位于信息链的后端,包含在Information Science内,知识向情报转化构成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图1)。大数据时代,数据可以跳过信息及知识的流程,直接转化为情报,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如应急事件决策支持),数据在简化的情报流程下可以直接转化为决策。与此同时,数据内容变得异常丰富,成为情报学研究的主要来源,各领域数据不仅横向关联、纵向延伸,也在实时发生着变化,由此构成了非线性流动和处于混沌状态的复杂数据流。对复杂数据流的强调彰显了情报学在大数据研究中的地位,对数据流的组织构成情报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可见,情报学研究在数据流向有序数据转化、数据向知识转化过程中便开始发挥作用,情报学的作用要前移,由此掌控复杂数据,将复杂数据流的组织及其向知识、情报单元转化纳入学科范
畴[21] ;此外,情报学的作用还要强调向后延伸,将决策支持功能作为重要的价值体现,这是对情报学研究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回应(图2)。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学科,应定位为:数据流中的Intelligence Studies,即情报学是控制数据流,并将其转化为面向决策支持服务的知识和情报的准学科。相比前大数据时代的显著变化是:情报学研究对象为复杂型数据,情报研究与服务的逻辑起点更加强调任务与问题驱动,情报流程在缩短,情报学科的价值在于遏制数据爆炸,以及基于此提供的智囊服务。这一学科定位,导致情报学教育体系和应用理论体系的变革:情报学教育体系有所改变,将数据科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作为情报学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报学应用理论有所革新,尤其是情报工作流程、方法以及机制、能力建设等要适应缩短的情报流程,在情报支持决策中将常规性和应急性过程并举,重视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学理论重建。
2)学科目标:依靠大数据为国家发展与安全服务
20世纪70—80年代,情报学注重为科技、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开展战略服务,以学术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符合当时的信息环境和国家发展战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国家发展与安全面临新挑战: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全面改革的关键时期,总体国家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情报学素来有为国谋略和强烈时代感的优良传统,在面向国家发展与安全环境的当下,情报学科的研究目标宜紧跟时代所需,把握并利用大数据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的机遇和保障。
情报学的学科目标应设定为:依靠大数据为国家发展与安全服务。情报学应成为大数据的“主人”,统领大数据的情报价值建构过程,通过情报检索和组织掌控大数据,通过转化将大数据变成知识和情报资源,从而提供情报保障,这是情报学的基础目标。情报学的终极目标是依赖于情报挖掘工具的支撑和情报服务能力的提升,成为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引导者。“引导”要求情报学具有主动意识、全局思维、大局胸怀和前瞻眼光,为建设防御型和进攻型相结合的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提供情报支持、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指引中充当智囊(图3)。
学科目标的实现需要情报研究能力的支撑。大数据时代,情报检索应重视面向不同类型和结构信息源的综合性跨库检索,强调静态存量检索的同时,还要加强流量监测型实时检索,实现智能化相关性匹配检索,构建情报检索系统来给予相应支持。情报组织也由结构化数据组织与处理向复杂结构数据扩
展[3] ,实现数据的融合与语义关联化组织,将复杂的大数据通过融合与序化方法转化为数据资源,并通过知识发现技术、情报挖掘技术以及相应的组织技术将其转化为知识和情报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知识单元与情报单元的提取,这一过程需要大数据组织与分析技术的推动。情报服务能力涉及的问题较多,包括“硬件”和“软件”服务能力两大方面,硬件包括情报机构、情报人员、情报体系建设等;软件包括相关的体制、机制与文化构建,以及情报分析工具的开发等。3)理论体系:面向大数据的情报学理论适应性革新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我国老一辈情报学家通过引进与本土化并举的方式,推动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如严怡
民[22] 提出科学交流理论体系,卢太宏[23] 提出SCU规范情报学理论体系,推动了大情报观的萌芽[24] 。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技术的冲击和学科交叉的产生,使情报学理论研究陷入混沌状态,偏离“大情报观”的初衷,理论研究开始泛化;步入21世纪,网络研究的蔚然成风进一步加深了情报学理论的泛化和偏离,理论体系不完善并向多元化发展[25] ,基本概念不统一、研究对象不明确[26] 等。此时的情报学理论已经成为情报学发展的桎梏。对情报学理论虚化、泛化问题的探讨在情报学界始终不绝于耳,如何构建情报学理论,并使之适应大数据时代情报学科建设和情报工作的发展趋势,这是当前情报学研究需重点关注的课题。理论的构建需要原理的支撑,马费成教
授[27] 提出的情报学六大原理(离散分布原理、相关性原理、有序性原理、省力原理、小世界原理和对数透视原理)揭示了情报学研究及其工作的基本机理,是情报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根基。叶鹰教授等[28] 曾建议用这些原理构成数据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共通理论内核。大数据时代,应将这些原理映射到大数据环境中,构建更加具体、更具适应性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由有序性原理探索面向情报揭示的数据序化理论,由相关性原理探索面向情报资源建设的数据关联化、融合化组织理论,由重组转化原理探索面向情报单元提取的数据转化理论,由离散分布原理探索面向情报采集的数据检索理论(如朝乐门[29] 提出的数据连续性理论),由对数透视原理探索面向情报挖掘的数据定量化分析理论,由最小努力原理探索面向情报工作的数据服务和用户研究理论等。此外,还需将信息科学三大理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数据科学基本理论与情报学原理融合起来,结合情报学科建设和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趋势,凝练出新的适应性理论。这些理论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彼此渗透、相互支撑,是情报学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4)知识体系:以“数据资源Intelligence化”为导向的知识体系框架
知识体系是情报学科建设的根基,情报工作开展的依据。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的知识体系与数据相融合,使情报学适应并利用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如前所述,面对情报学在信息浪潮冲击下研究的偏颇和失
衡[3] ,以包昌火等[30] 为代表的情报学者大声呼吁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提示情报学的知识体系要以Intelligence为导向。大数据时代,数据有望取代信息,成为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对象,Intelligence化的逻辑起点应向前移至数据领域。情报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明确三个问题:①知识体系以何为导向?基于情报的本质属性和情报工作的基本职能取向,情报学知识体系应以Intelligence为导向。大数据时代,Intelligence主要来自于数据,可将知识体系的导向定位到“数据资源的Intelligence化”。“(向)Intelligence(转)化”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方法类知识、流程类知识便构成了情报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②知识体系结构如何划分?遵循上述导向,情报学知识体系的结构宏观上应划分为基础理论类知识和应用类知识,前者重点在于把握数据运动规律,以及数据运动过程中情报组织、情报发现的相关问题,包括本质类知识、本体类知
识[31] 、组织类知识;后者侧重于如何将数据转化为情报行动,以及情报产品开发、情报传播等相关知识,包括行动类知识、实践类知识和应用场景类知识。③知识体系具体由哪些要素构成?知识体系的构成要素是在知识导向指引下,以知识结构为基本组织线索,通过文献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机器学习、专家调查以及对情报工作需求调研等手段,进行归纳总结而得。邓三鸿等[32] 的知识地图、王昊等[33] 的知识结构在此方面进行了一定尝试。情报学知识体系框架如表2所示。表2 情报学知识体系基本框架
一级结构 二级结构 三级结构 构成要素 基础理论类知识 本质类知识 原理、规律、特征 大数据相关性原理;大数据分布以及运行规律与特征等
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历史与发展趋势维度中各领域情报学发展规律与特征等
本体类知识 基本概念、基础理论 Intelligence的基本概念及其与信息、数据的关联性;不同领域的Intelligence概念的整合;情报学研究对象、方法、基本问题域,以及与大数据的关联性 组织类知识 关联性和情景性主导的数据序化、转化、融合 大数据描述与识别、分类/主题检索;大数据转化为情报过程中的方法类、流程类知识 应用类知识 行动类知识 积极情报、反情报、欺骗性情报 一体化行动管理类知识;制度类知识;能力类知识等 实践类知识 流程类、方法类 情报转化为行动的流程类、方法类知识;情报服务管理、传播类知识;情报机构管理类知识等 应用场景类知识 用户类,情景感知类 用户需求与管理类知识;情景模拟与感知类知识;情报分析类知识等 5)情报生产管理:流程化、标准化管理体系构建
情报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情报生产管理体系是应用导向的理论体系,情报生产的提出是受情报工程学的启发。情报工程学强调工程化思维在情报学研究范式、尤其是方法中的应用,研究内容逐渐具体化,已成为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对于情报工程学发展的最后一公里——“情报生产”强调不够,它是体现工程化思维、进一步突出情报学作为应用性学科的重要一环。
情报生产是将情报研究转化为情报产品进而向情报用户提供服务的过程,是情报成果转化的直接体现,强调的是情报产品化,以各类咨询报告(如分析报告、决策支持报告等)、情报分析工具等为主要形式,以用户定制为基本导向。情报生产涉及的要素较多,既包括作为生产方的情报分析人员、数据分析人员和领域专家,也包括作为情报产品接受方的用户,从情报产品到用户的传递渠道,以及情报产品的有效性评估;既包括情报产品自动化、智能化产出的专门的情报工具与方法,也包括作为支撑要素的数据资源建设。
将这些要素凝聚起来共同作用于某一特定情报产品生产,需要流程化与标准化管理。流程化是实现情报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组合优化的需要,标准化能够促进情报生产的规范化、生产力量的凝聚。情报生产的流程化管理体系需明确的是:情报生产过程中存在哪些基本要素,各要素的职责如何,各要素之间的知识流动问题,各要素之间协同与制衡的关系治理等。标准化管理体系主要是将情报生产中的各具体要素、流程和方法等进行统一标准化处理,这其中不仅包括相关术语,更为重要的是对情报生产的流程、程序进行标准化建模,如情报分析人员在情报生产流程中的定位、数据分析人员的介入、专家的职责以及发挥作用的时机等。此外,情报生产管理需建立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过程性情报产品有效性评估机制与指标体系,以此来优化生产管理过程。
3.2 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学科研究与应用
1)情报学研究:贯彻“数据即情报”理念
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如何将数据转化为情报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贯彻“数据即情报”的理念,实现数据向情报转化的“短、准、快”,即情报流程缩“短”,情报工作精“准”,情报成果“快”速产出。这就需要情报学研究做出如下改变:
第一,改变情报流程的组织线索。原有情报流程突出生命周期思想的应用,如“规划→搜集→分析→发布→评
估[21] ”。而在“数据即情报”理念下,更加侧重于数据直接转化为情报的技术实现,转化过程几乎不会有用户的参与;也可能是未经任何规划,无需经历程序化的发布、评估等环节,数据转化为情报成为一种“按需(On-demand)”活动。例如,在一个情报分析系统中,输入某一特定数据,系统自动反馈为相应的情报。此时,系统内部自动进行的运算为“全放方位数据采集和清洗→融合与关联化数据组织→数据建模与分析→数据诠释与可视化展示”。这需要强大的技术与工具支撑,如数据存储技术(Bigtable、GFS、NoSQL、Dynamo、HBase)、数据组织技术(MapReduce、语义关联技术、数据聚合与融合技术、高维数据降维技术)、情报发现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知识发现技术、话题演化分析技术)等;同时,需加强面向情报发现的分析工具研发。第二,加强情报成果的整合和专家系统的建设。在“数据即情报”理念下,情报研究的产出成果更具针对性、更加碎片化,成果展现形式可能是文字描述,也可能是可视化的图形,这一过程均由智能技术在一定算法下完成。在满足面向整体性、全局性情报需求时,情报成果应该被进一步整合,借助专家的领域知识进行更为科学、深刻和考虑人文环境的判读,并进行全局性把握。
第三,将跨学科研究落到实处。“数据即情报”理念下的情报学研究更加需要跨学科研究的支持,将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与情报学一道构成情报研究的基础,必须把握一点的是,情报学要在跨学科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引领这些学科的情报价值建构。
2)情报服务:融入大数据服务模式
Delen
等[34] 将大数据服务模式依次分为“数据即服务(DaaS)”、“信息即服务(IaaS)”和“分析即服务(AaaS)”(图4)。其中,DaaS和IaaS着重于数据、信息检索及其相关的服务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建立。作为大数据服务的高级模式,AaaS在前两者基础上,进行知识分析与服务,并以可视化形式加以展示。情报服务在大数据服务的底层可以为大数据的序化和融合提供理论与方法,大数据服务则可以为全方位数据检索与组织服务提供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在顶层的AaaS中,情报服务可以通过情报发现和决策服务深化大数据的知识服务并上升为情报服务,提高数据的利用价值,而大数据服务可以为情报发现和决策支持服务提供大数据技术与方法的支持。可以看出,情报服务融入大数据服务具有深厚的互动需求基础。融入大数据服务模式,最终有望形成两种情报服务模式:“情报资源即服务(Intelligence Resource-as- a-Service,IRaaS)”和“情报分析即服务(Intelligence Analytics-as-a-Service,IAaaS)”。IRaaS是将情报服务与大数据服务相融合后产生的情报资源作为基本载体,通过对情报资源的按需拓展计算,在保证情报资源处理速度和安全前提下,通过情报资源的融合,实现情报发现和服务的自动化,情报服务的按需供给,支持情报查询的优化处
理[35] 。IAaaS是在IRaaS以及情报服务与大数据服务融合的基础上,通过情报资源的深层关联和深度挖掘,实现情报分析的智能化处理,生产按需情报分析的产品。两者均以云计算为基础设施,符合“资源即服务(RaaS)—信息即服务(IaaS)—数据即服务(DaaS)—分析即服务(AaaS)”等“即服务”系列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技术要求。目前,开展真正的大数据服务实践的多为相关的数据与互联网公司。欲实现IAaaS和IRaaS,情报机构应通过共建实验室,人力资源交流,研究资源、技术资源和数据资源互换以及项目委托等方式与他们开展长期规划性合作。
3)高端情报人才培养:以情报实战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教育模式
大数据时代对情报人才有了新的需求。美国学者 Landon-Murra
y[36] 在“大数据与情报”一文中指出,情报学是培养数据科学家的学科;而《哈佛商业评论》指出,数据科学家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瞩目的职位[37] 。现如今情报人员应具备的素养应与数据的深度获取、关联、分析、利用紧密相关。这不仅对情报人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考验其敏锐把握快速多变的决策需求的能力。正如李辉等[38] 所言,对于情报工作来说,最重要的是具有分析能力、判读能力、熟悉情报业务、能独立开展情报判读、具备情报分析判断能力的人。培养大数据时代的高端情报人才可着重于以下三方面:首先,加强跨学科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在情报学博士招生工作中,鼓励从理工农医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优秀硕士毕业生进入情报学领域,来培养具有科技、医药、经济、管理等专业背景的高端情报人
才[3] ;另一方面,在课程体系建设中,以“情报”类课程为基础课,其他密切相关课程(如数据科学、统计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为必修课,以具体领域类学科为选修课(如管理学、金融学、社会学等),构建基础理论课(基础课+必修课)与应用理论课(选修课)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其次,加强情报实战训练,通过课程设置(如情景模拟课、实验类课程等)、推送到情报工作机构(如情报所)实践和引入具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专家来开展教学与辅导相结合的培训模式。最后,改革现有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如MOOC)来变革教学手段,加强实证类数据分析案例的教学内容。4 结 语
我国情报学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情报学的本质属性、理论内核和核心目标等学科建设的根基问题虽未完全定论,情报学在大数据的环境下的发展道路却应未雨绸缪,而且刻不容缓!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情报学学科定位、重新设计学科目标、重新完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重新构建应用理论体系,将大数据融入上述各要素中,推动情报学向智库型学科发展。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探究大数据环境下对情报学科相关要素的思维理念及实现方式的变革,以期为后续情报学学科建设提供启示。
参考文献
- 1
Gill P, Phythian M. What is intelligence stud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Public Affairs, 2016, 18(1): 5-19.
- 2
Marrin S. Improving intelligence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J].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6, 31(2): 266-279.
- 3
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回归[J]. 情报学报, 2017, 36(4): 331-337.
- 4
曾建勋, 魏来. 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学变革[J]. 情报学报, 2015, 34(1): 37-44.
- 5
彭知辉. 论公安情报学的学科属性及大数据环境下的变化[J]. 情报资料工作, 2017(5): 42-48.
- 6
韩毅, 李红. 大数据语境下情报学的坚守与拓展[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5): 47-52, 81.
- 7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 盛杨燕, 周涛,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 8
李广建, 化柏林. 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关系辨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4, 40(5): 14-22.
- 9
彭知辉. 论公安情报分析与大数据分析的融合[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10): 36-40, 73.
- 10
叶鹰, 武夷山. 情报学基础教程[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7-27.
- 11
马费成. 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J]. 情报学报, 2007, 26(1): 3-13.
- 12
化柏林, 李广建. 面向情报流程的情报方法体系构建[J]. 情报学报, 2016, 35(2): 177-188.
- 13
Manyika J, Chui M, Brown B, et al. 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R/OL]. [2018-04-07]. http://www. mckinsey. com/insights/business_technology/bid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 14
彭知辉. 情报流程研究: 述评与反思[J]. 情报学报, 2016, 35(10): 1110-1120.
- 15
Lim K. Big data and strategic intelligence[J].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6, 31(4): 619-635.
- 16
Chen H C, Chiang R H L, Storey V C.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From big data to big impact[J]. MIS Quarterly, 2012, 36(4): 1165-1188.
- 17
贺德方. 工程化思维下的科技情报研究范式——情报工程学探析[J]. 情报学报, 2014, 33(12): 1236-1241.
- 18
彭知辉. 数据: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的研究对象[J]. 情报学报, 2017, 36(2): 123-131.
- 19
周晓英. 情报学的形成和定位[J]. 情报资料工作, 2006(2): 5-10.
- 20
梁战平. 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历史性贡献[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4(4): 341-342, 399.
- 21
马费成. 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J]. 情报学报, 1996, 15(5): 22-28.
- 22
严怡民. 情报科学理论体系初探[J]. 情报科学, 1982, 3(3): 1-5.
- 23
卢太宏. 情报科学的三个研究规范[J]. 情报学报, 1987, 6(1): 20-22.
- 24
刘植惠. 评“大情报观”[J].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99(2): 69-71.
- 25
王芳. 情报学的范式变迁及元理论研究[J]. 情报学报, 2007, 26(5): 764-733.
- 26
王延飞, 赵柯然, 何芳. 重视智能技术, 凝练情报智慧——情报、智能、智慧关系辨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6, 39(2): 1-4.
- 27
马费成. 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J]. 情报学报, 2007, 26(1): 3-13.
- 28
叶鹰, 马费成. 数据科学兴起及其与信息科学的关联[J]. 情报学报, 2015, 34(6): 575-580.
- 29
朝乐门. 数据连续性: 未来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J]. 情报学报, 2016, 35(3): 227-236.
- 30
包昌火, 李艳. 情报缺失的中国情报学[J]. 情报学报, 2007, 26(1): 29-34.
- 31
杨雅芬. 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 41(2): 29-40.
- 32
邓三鸿, 金莹, 杨建林. 学科知识地图的构建——以图书、情报学为例[J]. 情报学报, 2006, 25(1): 3-8.
- 33
王昊, 邓三鸿, 苏新宁. 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知识结构的建立及其演化分析[J]. 情报学报, 2015, 34(2): 115-128.
- 34
Delen D, Demirkan H. Data, information and analytics as services[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3, 55(1): 359-363.
- 35
杨国立, 周鑫. “数据即服务”背景下图书情报机构科学数据服务的发展机遇[J]. 情报学报, 2017, 36(8): 772-780.
- 36
Landon-Murray M. Big data and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human capital and education[J].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2016, 9(2): 94-123.
- 37
Davenport T H, Patil D J. Data scientist: the sexiest job of the 21st centur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2, 90(10): 70.
- 38
李辉, 张惠娜, 侯元元, 等. 情报3.0时代科技情报服务能力研究——基于工程技术视角的服务能力四层结构模型(RIAC)[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3): 1-6.
- 1
摘要
情报学学科建设已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大数据对其影响很难被绕过。大数据环境将情报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在给情报学发展带来危机的同时,也为情报学地位的提升和研究力量的凝聚等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本文认为,破解危机、把握发展机遇的核心在于基于大数据思维的情报学学科发展。为此,本文以大数据思维为引导,重新思考了情报学学科定位、学科目标、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生产管理体系,以及情报研究、情报服务、情报人才培养等问题。
Abstrac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has been a major concern in academic circles.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has pushed intelligence studies into a new developmental stage. Although it has brought about a great crisis for intelligence studies, it has also brought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the cohesion of research resour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re of cracking the crisis and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lies in big data thinking i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ccordingly, big data thinking is considered a guide, and this article rethinks the discipline orientation, discipline objectives, theoretical systems, knowledge systems,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s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s well as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intelligence personnel training.